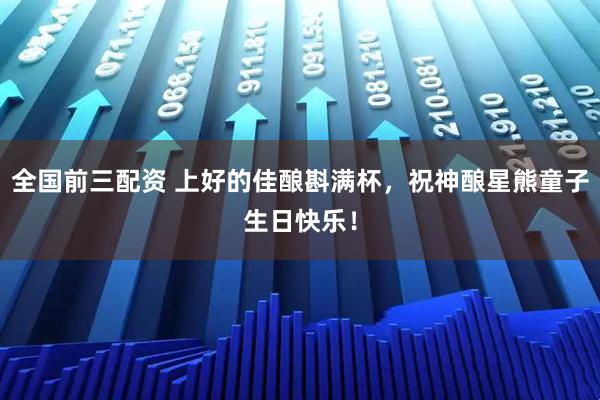想象一下,站在十公里外,用一枚炮弹精准击中六米宽的桥墩,这相当于在百米之外射中一部手机的宽度。 1985年秋天,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战区深处,解放军的一支炮兵部队就接到了这样一项任务:用老式的152毫米榴弹炮,在约九公里外,摧毁越南军队视为生命线的戈摆大桥。对于当时的常规火炮技术来说,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 这座戈摆大桥不是普通的小桥。它横跨在湍急的斋河上,连接着越南的黄连山省和河宣省。桥身全长大约一百二十米,桥面宽度却仅有六米。 它是越军在这一片区域至关重要的后勤运输通道,每天平均有十多辆运送武器弹药和粮食的军车通过股票公司配资,支撑着越军在河西地区大约一个营兵力的作战补给。如果我们能成功打掉这座桥,就能像掐住喉咙一样,切断斋河地区越军的补给线,有效减轻他们对扣林山方向我军西侧翼的威胁。 怎么打,成了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。有人提议派特种兵小队渗透过去炸桥。可仔细一琢磨,这条路太难走了。从边境出发,需要穿越近十公里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和层层设防的越军警戒线,成功的希望渺茫,付出的代价可能难以承受。
这座戈摆大桥不是普通的小桥。它横跨在湍急的斋河上,连接着越南的黄连山省和河宣省。桥身全长大约一百二十米,桥面宽度却仅有六米。 它是越军在这一片区域至关重要的后勤运输通道,每天平均有十多辆运送武器弹药和粮食的军车通过股票公司配资,支撑着越军在河西地区大约一个营兵力的作战补给。如果我们能成功打掉这座桥,就能像掐住喉咙一样,切断斋河地区越军的补给线,有效减轻他们对扣林山方向我军西侧翼的威胁。 怎么打,成了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。有人提议派特种兵小队渗透过去炸桥。可仔细一琢磨,这条路太难走了。从边境出发,需要穿越近十公里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和层层设防的越军警戒线,成功的希望渺茫,付出的代价可能难以承受。 另一个方案是用我们的大炮远程轰击。这个办法看起来直接些,但困难一点也不小。首先,我们炮兵阵地能够有效打击的最远距离,差不多正好卡在十公里这个极限上。其次,当时的火炮技术条件下,在这个极限距离上发射炮弹,落点的偏差很常见,动辄偏离目标五六十米甚至上百米。 而戈摆大桥呢?它最需要命中的关键部位,宽度仅仅六米。更困难的是,经过多次侦察发现,大桥南边的桥墩是直接浇筑在山体坚硬的岩石上的,极其牢固;只有北边的桥墩,基础是土质的,相对容易破坏,算是唯一能找到的薄弱点。 面对这些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,时任昆明军区文山军分区边防12团团长宋世华没有退缩。他亲自带着侦察分队和炮兵技术骨干,多次冒着风险前出到靠近边境的观察点。
另一个方案是用我们的大炮远程轰击。这个办法看起来直接些,但困难一点也不小。首先,我们炮兵阵地能够有效打击的最远距离,差不多正好卡在十公里这个极限上。其次,当时的火炮技术条件下,在这个极限距离上发射炮弹,落点的偏差很常见,动辄偏离目标五六十米甚至上百米。 而戈摆大桥呢?它最需要命中的关键部位,宽度仅仅六米。更困难的是,经过多次侦察发现,大桥南边的桥墩是直接浇筑在山体坚硬的岩石上的,极其牢固;只有北边的桥墩,基础是土质的,相对容易破坏,算是唯一能找到的薄弱点。 面对这些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,时任昆明军区文山军分区边防12团团长宋世华没有退缩。他亲自带着侦察分队和炮兵技术骨干,多次冒着风险前出到靠近边境的观察点。 他们一共进行了五次抵近侦察。每一次都小心翼翼,利用望远镜、指北针和测距仪,反复观测、计算和核对,一点一点地摸清了大桥的精确位置坐标,详细记录了守桥敌军的岗哨位置和活动规律。 边防12团还仔细研究了传回来的大桥照片和结构草图,分析判断,确认北桥墩确实是整座桥的弱点所在。技术上的准备工作更是细致到了极点。地图上标注的位置和实地测量总有出入,他们反复核对,修正这些细微的偏差。 由于炮弹生产批次不同,性能也可能有微小差别,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误差对精度的影响,他们特意从仓库里挑选了同一批号、同一炉钢生产的炮弹。几门即将投入战斗的152毫米榴弹炮,每一门都经过了技术人员的精心检查和校准,确保炮身稳定,瞄准装置精确无误。 边防12团制定的战术目标很明确:集中所有火力,先彻底摧毁北边那个土基桥墩;一旦桥墩垮塌,大桥结构必然受损,再抓住时机猛烈轰击桥面中部和南桥墩的连接部位,利用剧烈的爆炸震动彻底瓦解整座桥梁的承重结构。 而上级只批给了他们四十发炮弹,这意味着每一发炮弹都必须发挥最大效力,不能浪费。
他们一共进行了五次抵近侦察。每一次都小心翼翼,利用望远镜、指北针和测距仪,反复观测、计算和核对,一点一点地摸清了大桥的精确位置坐标,详细记录了守桥敌军的岗哨位置和活动规律。 边防12团还仔细研究了传回来的大桥照片和结构草图,分析判断,确认北桥墩确实是整座桥的弱点所在。技术上的准备工作更是细致到了极点。地图上标注的位置和实地测量总有出入,他们反复核对,修正这些细微的偏差。 由于炮弹生产批次不同,性能也可能有微小差别,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误差对精度的影响,他们特意从仓库里挑选了同一批号、同一炉钢生产的炮弹。几门即将投入战斗的152毫米榴弹炮,每一门都经过了技术人员的精心检查和校准,确保炮身稳定,瞄准装置精确无误。 边防12团制定的战术目标很明确:集中所有火力,先彻底摧毁北边那个土基桥墩;一旦桥墩垮塌,大桥结构必然受损,再抓住时机猛烈轰击桥面中部和南桥墩的连接部位,利用剧烈的爆炸震动彻底瓦解整座桥梁的承重结构。 而上级只批给了他们四十发炮弹,这意味着每一发炮弹都必须发挥最大效力,不能浪费。 1985年12月5日,中午12点30分。在精心构筑的炮兵阵地上,命令终于下达。第一发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冲出炮膛,飞向遥远的戈摆大桥。这发炮弹装的是瞬发引信,设定为一碰触目标就爆炸。 但它瞄准的并不是桥墩本身,而是故意打在了桥附近的空地上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爆炸腾起一团明显的烟尘。这团烟尘,给后方高地上负责观察的炮兵观察员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点。 观察员的眼睛紧盯着望远镜,迅速测算出弹着点实际偏离北桥墩大约二十米。这个关键的偏差数据,通过无线电立即传回了炮兵阵地。炮手们根据新的参数,快速调整了火炮的瞄准角度。 紧接着,第二发炮弹怒吼着出膛。这一次,炮弹如同长了眼睛,不偏不倚,狠狠地砸在了北桥墩上!剧烈的爆炸让桥墩表面碎石飞溅。还没等桥上的越军守兵完全反应过来,第三发和第四发炮弹几乎接踵而至。 这两发炮弹换装了延时引信,炮弹像钻头一样,在撞上桥墩的瞬间没有立刻爆炸,而是凭借巨大的动能钻进了桥墩内部深处,然后才猛烈引爆。 两声沉闷又巨大的爆炸声接连响起,北桥墩在内部冲击下被彻底炸塌,大块的混凝土和钢筋结构轰然倒塌。大桥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撑点,整个桥身开始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,剧烈地摇晃起来。阵地指挥员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战机,果断下令:“换短延期引信!集中火力,打桥面中间和南墩连接部!” 命令一下,炮击节奏骤然加快。从第五发到第十七发炮弹,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,以急促的射速,一发接着一发呼啸而出,飞向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桥。炮弹连续命中目标,桥面钢板被炸得卷曲断裂,混凝土碎块四处飞溅。 当第十七发炮弹在桥面中央轰然炸响后,这座曾经坚固的桥梁再也支撑不住自身的重量,伴随着刺耳的断裂声,如同被折断的脊梁,从中部轰然断裂,巨大的桥体段落翻滚着砸进斋河,激起冲天的水柱。 大桥垮塌激起的巨大水浪还没平息,越军设在附近山头的炮兵就开始了反击。炮弹呼啸着砸向我方阵地,炸起团团烟尘。可这一打,反而暴露了他们的位置。 我方炮兵观察员立刻锁定了这些火力点,迅速把坐标传回。很快,我们的炮弹就覆盖过去,重点打击了越军分布在1427高地、1559高地和老虎山一带的十多个暴露出来的阵地和工事点。
1985年12月5日,中午12点30分。在精心构筑的炮兵阵地上,命令终于下达。第一发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冲出炮膛,飞向遥远的戈摆大桥。这发炮弹装的是瞬发引信,设定为一碰触目标就爆炸。 但它瞄准的并不是桥墩本身,而是故意打在了桥附近的空地上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爆炸腾起一团明显的烟尘。这团烟尘,给后方高地上负责观察的炮兵观察员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点。 观察员的眼睛紧盯着望远镜,迅速测算出弹着点实际偏离北桥墩大约二十米。这个关键的偏差数据,通过无线电立即传回了炮兵阵地。炮手们根据新的参数,快速调整了火炮的瞄准角度。 紧接着,第二发炮弹怒吼着出膛。这一次,炮弹如同长了眼睛,不偏不倚,狠狠地砸在了北桥墩上!剧烈的爆炸让桥墩表面碎石飞溅。还没等桥上的越军守兵完全反应过来,第三发和第四发炮弹几乎接踵而至。 这两发炮弹换装了延时引信,炮弹像钻头一样,在撞上桥墩的瞬间没有立刻爆炸,而是凭借巨大的动能钻进了桥墩内部深处,然后才猛烈引爆。 两声沉闷又巨大的爆炸声接连响起,北桥墩在内部冲击下被彻底炸塌,大块的混凝土和钢筋结构轰然倒塌。大桥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撑点,整个桥身开始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,剧烈地摇晃起来。阵地指挥员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战机,果断下令:“换短延期引信!集中火力,打桥面中间和南墩连接部!” 命令一下,炮击节奏骤然加快。从第五发到第十七发炮弹,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,以急促的射速,一发接着一发呼啸而出,飞向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桥。炮弹连续命中目标,桥面钢板被炸得卷曲断裂,混凝土碎块四处飞溅。 当第十七发炮弹在桥面中央轰然炸响后,这座曾经坚固的桥梁再也支撑不住自身的重量,伴随着刺耳的断裂声,如同被折断的脊梁,从中部轰然断裂,巨大的桥体段落翻滚着砸进斋河,激起冲天的水柱。 大桥垮塌激起的巨大水浪还没平息,越军设在附近山头的炮兵就开始了反击。炮弹呼啸着砸向我方阵地,炸起团团烟尘。可这一打,反而暴露了他们的位置。 我方炮兵观察员立刻锁定了这些火力点,迅速把坐标传回。很快,我们的炮弹就覆盖过去,重点打击了越军分布在1427高地、1559高地和老虎山一带的十多个暴露出来的阵地和工事点。 这次反击作战,一共打掉了越军十来个目标,包括五栋简易营房、十个暗堡、七个机枪工事、三个掩蔽部、一个82无坐力炮阵地和一个观察所,越军士兵被炸得措手不及。炮击戈摆大桥的行动,加上这次反击作战,统计下来一共毙伤越军六十多人。 这还不算完,12月10日那天,发现越军偷偷摸摸想在被炸毁的大桥附近搭浮桥,我们的炮兵立刻又开了火。十二发炮弹砸过去,把刚搭出个样子的浮桥炸散了架,连带着打沉了他们一条运送材料的木船,又撂倒了四个敌人。 到了12月29日下午三点多,侦察发现桥头聚集了上百号越军士兵,还有不少骡马,看样子是想用原始办法运送物资过河。我们的炮弹再次呼啸而至,三十发炮弹砸进人群和物资堆里,炸死七人,炸毁了一些物资,剩下的敌人吓得四散奔逃,再也不敢露头。 这次精准炮击,从头到尾只用了十七发炮弹,就彻底摧毁了戈摆大桥。更重要的是,它像一把锋河西那个营的越军,弹药粮食运不进来,伤员也难以及时后送,战斗力一下子垮了大半。
这次反击作战,一共打掉了越军十来个目标,包括五栋简易营房、十个暗堡、七个机枪工事、三个掩蔽部、一个82无坐力炮阵地和一个观察所,越军士兵被炸得措手不及。炮击戈摆大桥的行动,加上这次反击作战,统计下来一共毙伤越军六十多人。 这还不算完,12月10日那天,发现越军偷偷摸摸想在被炸毁的大桥附近搭浮桥,我们的炮兵立刻又开了火。十二发炮弹砸过去,把刚搭出个样子的浮桥炸散了架,连带着打沉了他们一条运送材料的木船,又撂倒了四个敌人。 到了12月29日下午三点多,侦察发现桥头聚集了上百号越军士兵,还有不少骡马,看样子是想用原始办法运送物资过河。我们的炮弹再次呼啸而至,三十发炮弹砸进人群和物资堆里,炸死七人,炸毁了一些物资,剩下的敌人吓得四散奔逃,再也不敢露头。 这次精准炮击,从头到尾只用了十七发炮弹,就彻底摧毁了戈摆大桥。更重要的是,它像一把锋河西那个营的越军,弹药粮食运不进来,伤员也难以及时后送,战斗力一下子垮了大半。 整个斋河地区的敌军,东西方向的物资转运和兵力调动也彻底瘫痪,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进攻。扣林山方向我军西侧翼的压力,因此大大减轻。直接执行这次关键炮击任务的成都军区守备一师三团152榴弹炮2连1班,用他们精湛的技术和完美的执行,赢得了“神炮班”的光荣称号。这不仅仅是对他们一次战斗的褒奖,更是对老炮兵过硬专业能力的认可。 这场被后人称为“万米穿杨”的炮战奇迹,核心奥秘不在于用了多先进的武器,那几门152榴弹炮已经是快退役的老装备了,用的也是最普通的炮弹。 真正的关键,在于人,在于那份做到了极致的准备和战场上的冷静判断。宋世华团长带着人,前前后后冒了五次险去抵近侦察,才把大桥的精确位置、结构弱点和敌军布防摸得一清二楚。 技术员们一丝不苟,专门挑选同一批生产出来的炮弹,连细微的批次差异都尽量排除掉;对每门炮都做了最精细的检查和校准,确保它们处于最佳状态。
整个斋河地区的敌军,东西方向的物资转运和兵力调动也彻底瘫痪,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进攻。扣林山方向我军西侧翼的压力,因此大大减轻。直接执行这次关键炮击任务的成都军区守备一师三团152榴弹炮2连1班,用他们精湛的技术和完美的执行,赢得了“神炮班”的光荣称号。这不仅仅是对他们一次战斗的褒奖,更是对老炮兵过硬专业能力的认可。 这场被后人称为“万米穿杨”的炮战奇迹,核心奥秘不在于用了多先进的武器,那几门152榴弹炮已经是快退役的老装备了,用的也是最普通的炮弹。 真正的关键,在于人,在于那份做到了极致的准备和战场上的冷静判断。宋世华团长带着人,前前后后冒了五次险去抵近侦察,才把大桥的精确位置、结构弱点和敌军布防摸得一清二楚。 技术员们一丝不苟,专门挑选同一批生产出来的炮弹,连细微的批次差异都尽量排除掉;对每门炮都做了最精细的检查和校准,确保它们处于最佳状态。 战斗打响后,第一发炮弹故意打偏,用炸起的烟尘来修正瞄准点,这需要观察员眼疾手快、计算精准。发现北桥墩被炸塌、桥身开始剧烈摇晃时,指挥员立刻决定更换引信类型,集中火力猛攻桥面中部,这临机决断非常关键。这种依靠周密计算、严格操作和战场应变来弥补装备技术差距的做法,正是老炮兵的看家本领。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一年前的老山松毛岭,我军炮兵部队用排山倒海的炮火,一天之内就粉碎了越军六个团的轮番猛攻,让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。这两仗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:打仗股票公司配资,后勤线就是生命线,掐断了它,再凶悍的军队也得趴窝;炮火威力大固然重要,但打得准、打得巧,把力量用在刀刃上,才是制胜的关键。
战斗打响后,第一发炮弹故意打偏,用炸起的烟尘来修正瞄准点,这需要观察员眼疾手快、计算精准。发现北桥墩被炸塌、桥身开始剧烈摇晃时,指挥员立刻决定更换引信类型,集中火力猛攻桥面中部,这临机决断非常关键。这种依靠周密计算、严格操作和战场应变来弥补装备技术差距的做法,正是老炮兵的看家本领。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一年前的老山松毛岭,我军炮兵部队用排山倒海的炮火,一天之内就粉碎了越军六个团的轮番猛攻,让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。这两仗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:打仗股票公司配资,后勤线就是生命线,掐断了它,再凶悍的军队也得趴窝;炮火威力大固然重要,但打得准、打得巧,把力量用在刀刃上,才是制胜的关键。
金富宝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